转载:《长篇小说选刊》

柳冬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一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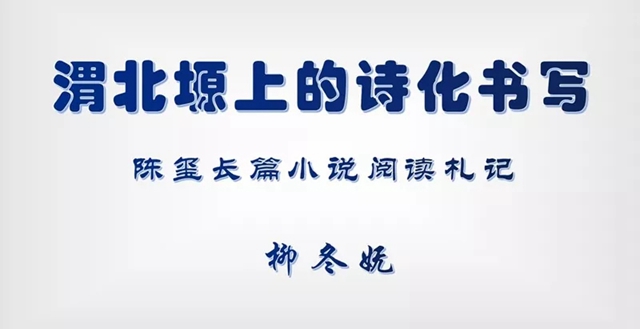
总结一个时代或一个城市的文学,历来是文学史家或文学理论家所不愿也不能忽略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鲁姆就主编过一套文学地图丛书,对巴黎、都柏林、伦敦、纽约、圣彼得堡等城市作家群的形成原因,从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个人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证,重点评述每座城市代表性作家的重要作品,努力保存城市文学创作的珍贵记忆。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是东莞文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非常时期,其文学实绩之丰厚,文学观念之驳杂,文学现象之多彩,文学影响之深广,远甚于以往任何时期。东莞作家的文学创作繁复而火爆,不同题材、体裁、风格、手法,包括不同载体和类型的文学作品,争妍斗艳,竞相展示,审美个性受到尊重,艺术探索获得鼓励,流派或群体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现象不断呈现,若干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层次。东莞作家群的整体崛起,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东莞作家群已经成为东莞醒目的城市文化符号。而作为东莞作家群的领头雁,陈玺的长篇小说创作特别引人瞩目,为东莞文学创作树立了标杆。陈玺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暮阳解套》《一抹沧桑》和《塬上童年》,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作家》《飞天》等杂志发表多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
作为著名的移民城市,一提到东莞,容易让人想起东莞的“打工文学”,但真正能够体现东莞移民特点的,恰恰不是“打工文学”,而是以陈玺以为首的“东莞移民作家”群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东莞迅速由一个香飘四季的农业县发展成为新兴的制造业名城,成为广东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者聚集东莞,他们在东莞工作、生活、感受、碰撞,形成了特有的打工文学现象。实际上比“打工文学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移民作家”陈玺、陈启文、胡海洋、杨双奇等人的长篇小说,每个人的故乡记忆构成了他们情感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来自湘西的土家族作家杨双奇创作的长篇小说《野性湘西》,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现代湘西的传奇故事,审视历史长河中湘西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裂变;来自江西的满族作家胡海洋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河拐大弯》,以江西“卓仁堂”末代传人——卓逸之的青葱成长为导线,揭示了一个延传百年的中医世家走向破败的精神根源,也揭示了国民精神这一持久伤口无药能医的历史渊源。来自湖南的作家陈启文创作了长篇小说《江洲义门》,展示了江州义门陈氏五百多年的家族建立、兴盛、最终几近灭亡的历史。东莞的“移民作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这恰恰是最重要的移民特征。这些作家都是携带着自己的精神原乡进入东莞的。陈玺的长篇小说《一抹沧桑》《塬上童年》对渭北乡村的书写,更让我们看到,好的移民作家大都有一个自己的写作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是精神意义上的。

陈玺的精神根据地是久远沧桑和凝重的三秦大地,是北部的豪放粗犷和南边的细腻婉约并蓄的关中大地,是化为作家生命底色的渭北塬上村落。陈玺在《一抹沧桑》的后记,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定的程度上,人就像一台计算机,故乡给了他社会化的第一个操作系统。”“人的第一套操作系统,会镶嵌在血脉中,构成了人的灵性的内核”。与故乡陕西的离散和聚合,形成了陈玺心灵世界非常复杂的“操作系统”,他对关中塬上的乡村生活有着特有的敏感性和直觉性。《塬上童年》写出了挖荠菜、摘洋槐花、做梭镖、捡麦穗等一桩桩的乡事,也写出了物质匮乏年代的乡村记忆。分油时,栓娃妈“将剩下的油倒进碗中,将瓶子翻过来,靠在铁锅的耳边,让油滴干净”。一滴油都舍不得浪费,连油桶壁上残留挂着的一点油,小伙伴们也要用“塌塌饼”揩个干净。乡村人家的油瓶,“人口多的家庭,用的是大一点的瓷壶,少部分是医院用过的葡萄糖输液瓶,大部分是蓝色高颈的西凤酒瓶子”。小说将物质匮乏年代乡里人的质朴、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是亲历者,很难捕捉到这样的生活细节。小说中对牧羊细节的描绘,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也表明了亲历经验的重要性。这样的生活细节,构成了陈玺小说的血肉,也正是触动他情感的最为敏感的按钮。他的小说是故地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的诗性书写,是形塑族性记忆的重要文化想象场域和美学形式。近八十万字的《一抹沧桑》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鸿篇巨制,陈玺以工笔与写意融合的手法,以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为背景,描写了陕西关中渭北塬上几户农家日作日息的生活形态和情感姿态,还原了华夏数千年的农耕生活,充分展现了作家对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观察与积累。渭北塬上的风俗、习惯、饮食、戏曲等,贯穿始终;阉牛、劁猪、配种、杀猪、爆米花等,不离其中;挼泥、放炮、掏鸟窝、骑驴、偷瓜等,点缀其间。岁月流转,世事变迁,一代代人耕耘不已,一个个家庭悲欢离合。在时间的长河中,陈老五、马九、智亮、麻娃、宏斌、志发……诸多人物构成了典型的中国农民群像,他们悲欢离合的命运走向与塬上村落的纠缠相扣,彼此无法摆脱,他们以汗水、眼泪和血,给中国的乡土大地烙下一抹沧桑。陈玺让我们体会到时代变革阵痛与人们心灵震颤之间的内在关系,感受到作家对乡土中国境况和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书写了赤黄大地上如蚁一样千百年来支撑着民族前行,并被历史的印记长期忽视的一隅苍生”。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称赞《一抹沧桑》“是一部建筑在童年记忆基础上的重返乡土之作。由于作者身处南国,遥望故乡,文化的差异增添了怀旧的冲动,因而这也是一部充盈着现代乡愁之作”。著名作家邱华栋认为,“陕西出文学大家,陕西作家善于浓墨重彩地书写八百里秦川的世事动荡、白云苍狗。即使比之于《白鹿原》《秦腔》这样的乡土文学巨作,《一抹沧桑》仍然有其独到的让人回味的地方。陈玺悠长的叙述语调,挥之不去的乡愁别绪,使这部近百万字的皇皇大作,既有工笔画的整饬、明丽,又具有写意画的氤氲、挥洒,可以视之为中国乡土文学又一代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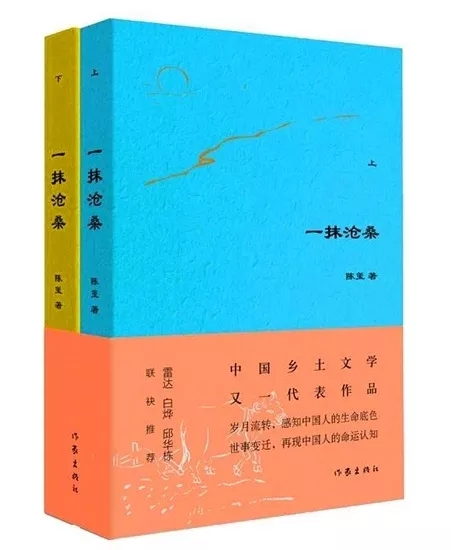
在《一抹沧桑》里,我们看到陈玺对长篇小说史诗品格的审美追求,富于强大的思想张力和绚丽的美学光泽。在对塬上世界的书写上,陈玺采取了诗性的表达方式。“诗性”是陈玺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从《一抹沧桑》到《塬上童年》,构成了一幅壮观的“诗性”小说场面,如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营造、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都体现了小说的诗化特征。陈玺把某些文体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将小说用诗和散文的笔法写成,使其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体现出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相互渗透。长篇小说《塬上童年》原发《中国作家》文学版2018年5期,作品发表后引起文坛广泛关注。小说以懵懂少年的视角,勾勒出了乡间孩童嬉戏的童年岁月,描绘了一幅具有时代特色的塬上全景风情画。《塬上童年》可以称之为“诗化小说”,也可以称之为一部长篇系列散文诗,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最大限度的逼近诗,具有的诗的意境和情致。它与传统小说在语言的运用、结构的设置、叙述的方式及人物形象的刻画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追求目标和审美特征。《塬上童年》的自序,刊发2019年08月11日的《光明日报》,这篇序言实际上就是一篇散文诗:
上世纪70年代初,村子里的孩子像水中的蝌蚪,在阳春三月消融的麦田中拾雁粪,挑野菜,爬树采洋槐花;麦收季节,他们穿着白衫蓝裤,扛着红缨枪,在村口站岗放哨,或是跟着妈妈踩着晨露,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捡麦穗;仲夏时节,他们游曳在田间壕渠,偷西瓜,摸鸟窝,坐在树梢瞭望,潜到水中嬉戏;秋雨中,他们挖红薯,拾棉花,收玉米,种小麦;严冬,他们缩着脖子,猫在用蛇皮袋堵着窗户的教室中,盯着讲台上的老师,思量着溜到“平整土地”的工地上混碗面吃;过年了,盼望大人们工地回来,更期盼着生产队杀猪。
春节,回到塬上故里。站在村东头的壕边,朝南瞭望,老村头的槐树恰似一位在寒风中打着喷嚏的老人,摇摆着萧瑟枯枝。一群乌鸦围着树梢的窝,叽叽喳喳地盘旋着,我瞬间想起童年掏鸟窝的情景。在荒草丛生的院落里,我找到已经断筋生锈的弹弓和链子枪,寻到了铁环。除夕夜,依旧是雪花纷飞,炮竹声声。我裹着大衣,来到童年几个玩伴的家里,憨憨的笑容和木讷的表情,客套地寒暄,我带着沉积在心里的热情,试图打开童年的话题。回到家里,我带着侄子放鞭炮,我似乎看到孩提时,村子的人站在门前,品评着每家每户的春联和炮竹。
从老家归来,我依旧陷入追忆的旋涡中,我要用键盘敲出一幅童年的画卷。乡村渐渐远去,四十多年,古旧沧桑的华夏大地发生了巨变,浓缩着时代印记的渭北塬上一群孩子的故事,必将沉寂在历史的洪流中。而我希望将这份故乡的馈赠永远地留存下来。
关中渭北的塬上,是那个年代人们的集体记忆,青涩和懵懂中有着稚嫩的遐想。就像故乡的老汉吆着老黄牛犁地,有的犁得深一些,有的用铧尖划道渠,就过去了,文学只有在对生活的深耕细作中,才会感悟到天地自然的韵致,感悟到将生命皈依于这片土地的人们的情感。
给童年一个浮标,年老体弱的时候,大家坐在岸上,瞭望着漂曳的浮标,那是弥足珍贵的生命记忆;给童年一个浮标,让垂钓的少年,记住几十年前,他们的父辈曾像蝌蚪一样,在涝池中嬉戏,像牛犊一般,在大人的督促和责斥下渐渐成长。
陈玺的这篇序言不仅交代了写作《塬上童年》的缘起,而且本身就用散文诗的笔法,写童年的生活,追忆成长的历程,生活气息浓郁。序跋是陈玺长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序跋为切入角度,能够管窥到陈玺的诗学追求,序跋与文本之间的有着密切的互文性关系。陈玺为《一抹沧桑》所写的《后记》,其实也是一篇语言十分优美的散文诗,对渭北塬上景物的描写是非常传神的。渭北瓦楞上的雨线,在创作主体的心理意识层面聚合而成一种心绪,一种不舍的情怀。陈玺的小说都存在着这种情绪结构,这种情绪结构在本质上是属于诗的。从结构形态上,陈玺的“诗性”小说《塬上童年》不再讲究叙事的连贯性,情节的集中紧凑等特点,而采用了诗化、散文化的情调、情绪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严谨性,而是通过创造零碎的场景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来淡化叙事情节,将一种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小说当中,以深层的内在意蕴将生活的片段、简单的故事情节以及复杂的情感思绪贯穿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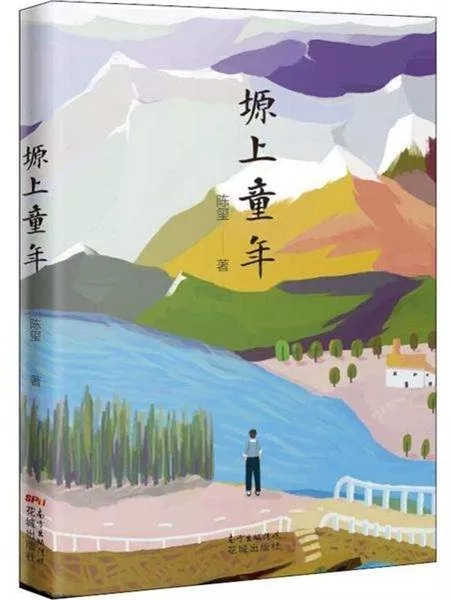
与传统小说相比,陈玺的“诗性”小说将语言的诗化放在首要位置,其语言隽永含蓄及精炼自然,节奏感强,富有内在韵律,而且能构成抒情意象,具有深刻宏阔的主题意蕴,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音乐美。《塬上童年》通过栓娃的视角,描绘了陕西大地所特有的景观意象,给人的视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低头一看,下面是一望无际翠绿翻滚的麦浪和散落在田间地头亦如麻点一样的人影。成群的蜜蜂,颤抖着翼,嘤嘤嗡嗡穿梭在花蕾间,用触须撩着沾着露水的点点花蕊。平视北望,塬下是一条宽阔的黛色的川道,川道北起的缓坡尽头是沉睡在大地上,守护着这片水土的端秀威仪的姑婆陵。转身南望,土塬南沿下,是飘着白雾的八百里秦川,中间镶嵌着一道白啦啦的水带,南岸是雄浑逶迤的秦岭山峦。”陈玺借鉴诗歌“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情绪流动的结构方式来组织心绪,诗意的语言展现出的是一幅雄奇山水图。《一抹沧桑》中,通过孙蛋的视角,将景观意象描写与生命意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坐在摇晃的汽车里,看着昏黄光晕下的灰秃秃的原野,孙蛋想到了这厚厚的黄土就像铺在地壳上的一层海绵一样,逝去的先辈将通过慢慢腐朽的棺木,最终融化在厚土中,黏黏的黄土阻隔了肉身的下渗,他们最终变成了肥料,滋润着田禾树苗,通过自然的轮回,成了另一种生命存在。”这种富有深味的诗的语言,这种鲁迅《野草》式的笔法,《野草》式的生命沉思,让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变成了抒情诗人,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发展的轨迹及情绪流动来组织结构,从而凸现出诗的抒情结构。小说人物与辽阔苍茫、粗犷坦荡、深邃博大的厚厚黄土精神容二为一。在这里,厚厚黄土成为乡土中国的精神象征。陈玺善于将人生观寄寓于风景的描画中,而从情感的抒发中追问生命的意义,我们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以遇见人格化的自然和自然物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