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入开展中宣部“百社千校书香童年”全民阅读活动,促进书香校园建设,推动“书香岭南幸福广东”全民阅读,广东教育学会于近期举办了第五届广东省中小学生“寒假读一本好书”活动。东莞作家陈玺的长篇小说《塬上童年》入选本次活动推荐书目。
本次推荐书目由专家审议,类型涵盖诗歌、童话故事、绘本、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多种少儿读物。图书内容健康向上,讲品质、讲格调、讲责任,文学审美价值高,可读性强。在此书单出炉之际,为你解读陈玺的长篇小说《塬上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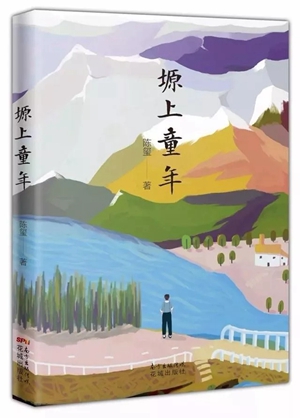
长篇小说《塬上童年》原发《中国作家》文学版2018年5期,作品发表后引起文坛广泛关注,2018年1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塬上童年》以懵懂少年的视角,勾勒出了乡间孩童嬉戏的童年岁月,描绘了一幅具有时代特色的塬上全景风情画。作品将童年的叙事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审美情趣,通过对童年生活的描写,从而给读者以美感和陶醉,集合阅读愈合浮躁心灵美与哲学思辨美。无论是对现实乡土的客观描摹,还是对乡土历史的重新审视,对小人物命运浮沉的展示,都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关怀,体现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性的叩问和对自由的渴望。《塬上童年》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描写,进一步去探寻乡土人物的纯真美好。这种心灵的淳朴、纯净和美好,正是现代城市社会所欠缺的。作品中淡淡的哀愁与温暖交织在一起,充满着迷人的气息。
相关评论:
巴尔扎克谈论美学和文学,都有很强的哲学意识和科学意识,他要分析人生是什么。我们现在过多强调感性神秘的东西,魔幻现实主义以后,我们几乎不用真实来写作,凭着混乱的想象来写作。《塬上童年》就是客观性与诗意性,非常好的融合,科学精神与文学精神和谐的融为一体,体现在写实上。我觉得小说的结构,人物关系,包括描写叙述中,一定有一种几乎科学一样的规律和客观性,不容你去漠视和随意对待。恩格斯讲过,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我觉得这个解剖可能就是医学精神,同样没有解剖,就没有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可能这个规律是多模式的。
这部小说里,作者的这种科学元素,使他非常正确的避免了我们当下小说写作中流行的一些可能属于误区或者是方向上的问题。我们现在小说,基本上就是主观和任性的想象,细节的堆积,没有意义感。陈玺的描写从容耐心,准确有力,他非常明白他描写的对象,他想象和对记忆的还原非常准确,非常清晰。这种强大的记忆力,对他描写的内容细节以及人物清晰准确的握度,在陈玺的笔下都达到了很成熟很自觉的水平。从结构来讲,《塬上童年》写一年四季,从春天写到冬天,在时间的向度上,以事件的块状搭结构,时间在流逝,生活却是在缓慢甚至是静止的状态下演绎。作者的叙事是缓慢而坚实的,态度是沉着而诚实的。读这部小说,你不会觉得文字是虚假的,会激活你相似的记忆,觉得他是可信的。
我读这部书,就像读《呼兰河传》,它们的结构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强大连续主导性的情节,就是儿童的记忆,一个一个清晰的画面呈现出来,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以儿童的眼睛看到的,纯真的清晰的和有趣的。像李国平刚才讲的,这一切都没有恶意,这里面写了很坏的人,整人的人,作者都没有强调内心的恶。关于太阳几次的描写,都是儿童的视角,是亲切可爱和纯真的。这部小说,读的过程当中,非常吸引我。
陈玺的小说是关中文化性格,文学气质非常成熟而完美的一个体现,深沉内敛,我是很喜欢的。陈玺出手真是不凡,作为一个陕西人,我非常高兴可以在北京开这个研讨会。有很多好话去讲,不觉得肉麻,不觉得违心,很开心。
——《文学评论》副主编、评论家李建军
这部小说,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强大的写实能力。我以前认为,写实渐渐过时了,那种魅力应该消失了。看了《塬上童年》,这个想法要修正。纯写实也会有魅力,关键是你写实,写的对不对,写的对就会有魅力。《塬上童年》我觉得写的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这些经历是他直接参与的,直接观察到的,这个生活不是他瞎编的,完全是真实的。一部小说里,发现几个好的细节,我们就喜欢得了不得,就很兴奋。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是细节,布满了细节,处处都是细节。而且他的叙事工夫,是百科全书似的,放羊、杀猪、腌牛都是细节,每一个过程都有头有尾的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这种叙事工夫,很了不得,我还没有看到叙事功底在长篇小说达到这个程度的,不多见。
二:写出了一个生动传神的儿童世界。我同意王山的观点,它不是儿童文学,他在以孩子王栓和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儿童生活中,融入了成人社会生活,写到了站岗放哨,栓和游泳的时候说,我这个泳姿是毛主席的游姿,给孩子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影响,包括戴红领巾,对英雄行为的模仿等等。这个儿童世界非常有趣、生动。
三:有时代的印迹。开始看的时候,好像没有时代感,看到后面,时代的印记非常自然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捡麦穗的时候,妈妈为了哄孩子多捡一会儿,说你想不想吃面片汤,想吃就多呆一会儿。民权偷窥小明的妈妈,被小明的爸爸打坏了,变成了傻子。虎子虐待媳妇,致使她死亡。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对百姓日常生活构成的影响。他不是附加上的,处理得非常好。
四:群像式的群体生活的呈现。人物形象的确立和人物命运的揭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包括爷爷善良地对待别人,爸爸受爷爷的影响,那种懦弱的性格,批斗时他默默的承受,奶奶对孙子的呵护溺爱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是在日常生活波澜不惊的描写中就完成的,我觉得非常好。
整个小说看了后,我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我觉得有一点像,虽然是一个男作者,但是他对生活描写的细致程度,非常到位。我非常喜欢,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讨论这部小说,对我们当前的创作,对小说的理解,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作家》杂志社主编宗仁发
我读陈玺的小说,有些篇章几乎要落泪,他是如此地写出了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地理,一种童年记忆,乡村的记忆,泥土的气息,童年的苦涩和童年的陶醉。我们都经历了乡村的70年代,陈玺的情感记忆,几乎也是我的情感记忆,我相信这部小说也会召唤在座许多人的情感记忆。陈玺具有双重思维,就是双重的心理结构。我们看他很粗犷,实际上粗犷中,他有非常细腻的那一面,他较好地处理了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关系。陈玺写作的时候,一定有给他人生底色的文化心理,还有单纯和复杂的怀念,所以,我把陈玺的小说,看作故乡对他的馈赠,又看作他对故乡的回报。
第二,有一类小说,我们叫做宏大叙事,大开大合,就举我们陕西的例子,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小说写刻骨铭心的记忆,历史社会时代的变迁,从北京传过来遥远的雷声,必须要经过人物内心的感受和情感的折射,才可以写出。有一种小说,可以粗线条的读,无伤大雅,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他写的是什么;有一类小说只有耐心的读,细读才可以体味,像宗仁发老师刚才说的,陈玺小说的细节非常细腻,非常有血肉感,比如说汪曾祺的小说。还有一类小说,有着另一类的美学风格,以还原生活为主,我借用一个词,叫做写得低调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对文明的挽留,比如说刘亮程和付秀莹的小说,这些在陈玺的小说中,都可以隐约地读到。在陈玺小说中,我们可以独读出细腻之外的厚重。陈玺的小说是那种服从于召唤的小说:少年的召唤,故乡的召唤,内心深处的召唤。他的写作是有功力的,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凸显质感,非许多职业作家的飘忽,这个小说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非许多职业作家飘忽游移所能比的,显示出他的文化地理意识。《一抹沧桑》的开篇,有一点大手笔的意味,他在文本中更注重具像而不是抽象。陈玺经常不动声色的写出了苦涩的良善,和善良的苦涩。他的作品不是不写政治风云,他作品不是纯粹的中国话,农村图,他只写遥远的背景人生,经过亲情乡情乡村伦理折射之后,在乡村的回响,通过少年的眼光,传导出淡淡的忧伤,写出心智的成长。比如他写麦客时,从小孩悠悠的感伤中,传导出少年品性的成长。
这部作品没有我们通常读的乡土叙述的断裂感,没有激烈的争斗,没有仇恨,更多的是亲情乡情植物情土地之情。这部作品也是有批评性的,但是总体是暖色调的。陈玺这两部作品是感恩之作。如果把《一抹沧桑》和《塬上童年》当成一个姊妹篇,当成一个整体看,有一个命题在这个作品里面他没有写出,但是几乎呼之欲出,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作者的经历,佐证了这一点,70年代乡村生活也有这个命题。这部作品是怀旧之作,但是怀旧里面有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感受,整体判断。
——《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

作者简介:
陈玺,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任东莞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暮阳解套》,2017年7月,出版长篇小说《一抹沧桑》,2018年11月,出版长篇小说《塬上童年》。2016年在《中国作家》发表中篇小说《菜籽案》、电影剧本《油菜花开》、长篇小说《一抹沧桑》。2017年在《北京文学》《作家》和《飞天》等刊物刊发小说《雪域情殇》《一抹烟尘》《一路向西》等。2017年12月,由广东作协和作家出版社,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一抹沧桑》研讨会。2018年5月,长篇小说《塬上童年》发于表《中国作家》。



